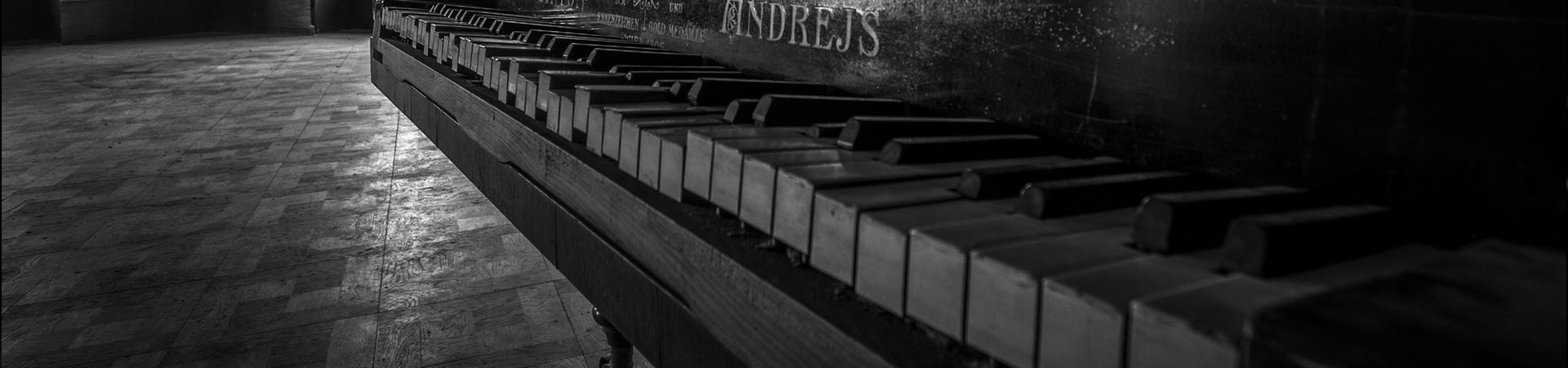

问答孙颖迪
问:过去最高兴的事?
答:付出的努力获得别人的认同。
问:未来最想做的事?
答:我想成就艺术上的圆通,而非做单一的古典音乐家。也因此,我将自己与其他钢琴家区分开来。虽然我学的是西方的音乐语言,但认为自己骨子里是个传统的中国人;我觉得中与西、古典音乐与其他门类艺术之间,一定存在相通之处,想把它们很好地结合起来。
问:最享受的事?
答:接受观众的掌声或是在禅林的山房中喝茶。
问:未来最希望得到什么样的支持?
答:宽容、宽松的演出环境,以及能让我独立思考、创作的空间。
问:工作以外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答:比较喜欢无拘无束、随性自然的生活状态。演出、旅行已经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若有空闲,最喜欢宅在家里。最近三四年,对《红楼梦》,更确切地讲是《石头记》,突然十分痴迷起来。
孙颖迪很少跟人说起,李斯特国际钢琴比赛前,他曾在一家名为jzclub的爵士酒吧兼职演奏。白天端坐学校琴房,勤练古典,晚上潜入jzclub,用爵士的随心所至释放自己,一周三四次,一晃两三年。
彼时,孙颖迪的“出格”让老师大跌眼镜;而他自己回想那段时日,亦觉得有些不可思议:愈夜愈美丽本不与他的生活轨迹重合。孙颖迪至今无法说清,那样的逗留里究竟藏着他怎样的心绪,但可以肯定,不是为了生计;“或许我到底是喜欢爵士乐的,家中的爵士唱片甚至多过古典乐唱片;又或许,出于一种怀才不遇的感慨,爵士乐本是疗伤音乐。”
午夜过后,客人渐渐散去,酒吧开始了音乐人即兴演出的时段。那最让孙颖迪享受,脱下面具,他任由自己变成音乐疯子。孙颖迪还记得,有一回一位同在酒吧驻演的新加坡朋友对他说:你的舞台不应该只在jzclub。这话竟令他彻夜难眠。
应该说,孙颖迪当算循规蹈矩的模范学生。从上海音乐学院附小、附中一直念到本科、硕士,及至工作,亦是选择留在母校教书。从小到大,他都是班里的种子选手,除了进附小时考过一回试,此后的求学路上全是绿灯―――一次次被保送。
但不知是逃避还是叛逆,身为学院培养的种子选手,他却惟独在钢琴比赛这件事上提不起兴致。虽然人们常说,比赛是通往成功的捷径,但孙颖迪抵触,他的参赛履历,几行字就能写尽―――8岁那年参加过上海青少年钢琴大奖赛,下一次便飞跨14年,跳到了2002年第二届中国“金钟奖”。
2005年开始攻读硕士的孙颖迪,此前从未考虑过“出路”,但那难以入眠的一夜不期而至,把他拉回现实,心头隐隐浮起不甘:二十四五岁了,除了拿奖学金,似乎没有什么成绩可以证明自己……虽然还看不清未来的方向,但他知道自己不愿仅仅做钢琴家教、做酒吧兼职演奏。于是,当恩师盛一奇教授再次鼓励他报名参加国际比赛时,孙颖迪报了名,斩钉截铁。他坦言,前途未卜的感觉不太好,我需要一个让自己爆发的时机。这个比赛,便是第七届李斯特国际钢琴比赛。
李斯特大赛,让孙颖迪一举冲进了西方主流音乐圈。但对于获奖和扑面而来的种种,他没多想,只觉如释重负。
有人说,孙颖迪能在这样一个素以高难度著称的赛事中脱颖而出,除了他在古典音乐上的修为与实力,或许也与他的爵士乐演奏经历分不开。因为比到最后,定乾坤的一着,是《匈牙利钢琴狂想曲第二首》中一段两三分钟即兴的华彩段落。孙颖迪放得很开,切换到了音乐疯子的状态,不知那一刻他是否想到在jzclub的那么多个夜晚。赛后,所有评委意见一致―――“声音非常漂亮,变化非常多”。他不仅胜在完美无瑕的准确度,更胜在闪烁敏捷的乐思,以及与乐队的默契互动。
现在,孙颖迪出镜率挺高,玩跨界、玩混搭,玩即兴弹奏,用钢琴与昆曲、与民歌、与现代舞配。见了他,此前关于他的种种想象竟被彻底颠覆。尝试着一连串“闹腾”的他,不张扬,显得儒雅,甚至内敛。初秋的上海,空气微凉,坐在我对面的孙颖迪,戴副眼镜,一身休闲西装,眉宇间书卷气很浓,笑起来还有几分卡通式的乖巧。他说话不紧不慢、不温不火,时常会把话题扯得很远。
但无论思绪飘到多远,孙颖迪都非常清楚现在的自己在做什么。投身古典音乐,他时刻准备着失望:属于古典音乐的黄金年代已然过去,自己能够赢得分量十足的李斯特大奖,却无论再过多少年也没法达到李斯特传奇式的辉煌。孙颖迪谢绝媒体给予自己“钢琴王子”的加冕,他需要一个更自由更开阔的发挥空间。
他很清醒,“炫技只是廉价的辉煌”。于他,更愿意将古典音乐化入生活,和他同样喜欢的爵士、茶道等等一起,渗透进平常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