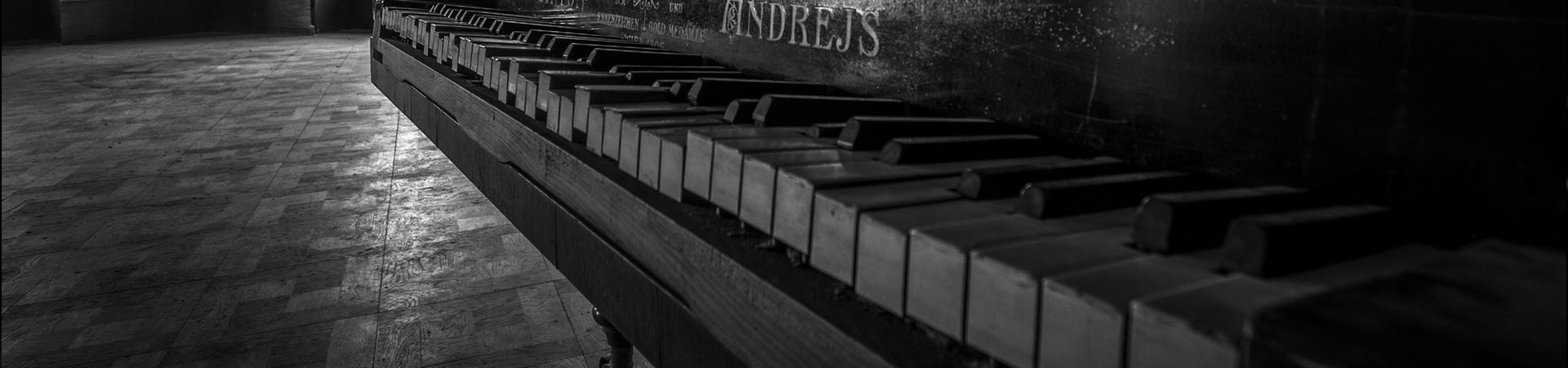音乐欣赏条件论
就“音乐欣赏”而言,这个命题应当具有两个主要的关系项,即音乐成品和欣赏者。它必然首先具有音乐成品是可以被欣赏的这一先决条件。
一般来说,音乐是创作者(作曲家和演奏唱家)对现实生活以及作品感受的一种表现,但对欣赏者来讲,则是一种美感经验的艺术传达。这种“表现”和“传达”是以音乐成品为媒介来完成的。音乐成品的欣赏,又是一对互为对象的美学范畴。它包括:创作者的审美——美感信息的可传达性——欣赏者的审美欣赏能力——欣赏者的审美再创造这样一种四重组合关系。从”接受美学“的观点来看,包括音乐在内的任何文艺作品,要为欣赏者所欣赏,它本身就必须具有可传达性(或称可欣赏性)。亦即创作者作出的音乐成品本身的内容、性质及潜在的功能已具有了引导和感人的艺术力量。而且,这个艺术力量的源泉——那些与音乐成品有关的,既包括音乐成品中文化的与音乐的两方面因素内容的科学性、合理性是经过无数音乐家不断梳理、排列和传播,被欣赏者不断接受和排斥,再被历史和时间不断检验或淘汰后存在的。这些作品是人类生活实践和思想感情,经过作曲家心灵的孕育和音乐这种传达形式相结合,以音乐表演为媒介,以音响美的成品形态呈现在欣赏者耳际的,它们的美,历史是以其音响和艺术形式、感情内涵和思想意义等得到包括音乐创作、评论和研究者在内的欣赏者广泛认同和选举。由于音乐欣赏的这个特点,才决定了用于欣赏的对象均已经是即具有可欣赏性,又具有推荐价值的优秀音乐成品(这里所说的可欣赏性和推荐价值是指包括成品形式和创作手段,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在内的这些东西,但在更多情况下是针对音乐成品的美感与艺术欣赏价值而言的)。
当音乐成品具有可欣赏性这一前提既已确立,随之而来应是欣赏者必须具有审美欣赏能力来与之相适应。提高对古今中外音乐佳作的欣赏能力,培养欣赏优秀音乐成品的慧眼灵心,是音乐欣赏研究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也是提高全民族审美素质的一个重要内容。
音乐欣赏能力的提高有赖于欣赏者具有必要的知识准备和合理的知识结构。在这里,音乐本身的知识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有一定的社会生活和感情经验的积累,特别是包括对音乐本身的美学特征和艺术规律的了解。如欣赏古典音乐作品,由于时代的不同,生活的变异,特别是很多创作者在创作时总会因这种或那种的原因将自己的灵感来源、创作意图等隐藏起来,因此就更需要欣赏者有充分的知识储备,对这些内容加以了解,才能准确、深刻的欣赏音乐获得美感。如从众多历史文献中可看到,贝多芬最富于独创性的《升C小调钢琴奏鸣曲》是集中反映贝氏心灵深处的孤独和悲伤情绪的作品。遗憾的是,德国诗人路德维希•莱尔什塔勃却把这部悲剧性的作品仅根据对乐曲某部分的感受比作是“瑞士琉森湖上的月光”。由于他倡议,乐曲还被题名《月光奏鸣曲》。以后,关于这首乐曲又被出版商附会出一则感人的《贝多芬与盲女》的故事大加宣传。其实,在该曲的流传过程中,不止一次有人提出不同意见,其中以俄国钢琴家安东•鲁宾斯坦坚决表示抗议,他指出:“月光要求某种幻想的、凄凉的、沉思的、宁静的音乐形象••••••而《升C小调奏鸣曲》第一章中,第一个音符至最后一个音符都是悲剧性的(升C小调暗示了这一点)。”其思想相当符合于自然辨证法。虽显然,关于“月光”一类的感受和那篇“动人的故事”,固然是欣赏者因直感失于偏,也应是由于知识欠缺所造成的失误,从根本上违背了原作的感情性质。
除了一般的社会生活知识和书本知识之外,欣赏者还应具备一些描绘性音乐语言表现方法方面的知识。在音乐中,描绘性的音乐语言可以刻画各种人物和动物的形象,描绘大自然景物,叙述事件;也可以把人们带到各种客观境界,让人感受到不同人物在不同的事件、情形中的活动、发展,以及感情或性格的发展、变化;甚至还可以把人带入鬼怪或神话世界中去,音乐在这些方面的描绘手法并不亚于其他艺术形式,且富有特色。如音乐对人物或动物的形象描绘,主要是通过对其性格特征的摸拟并结合乐器的不同音色特点来造成一种听觉形象等,使欣赏者能通过对相关生活情形与情绪的想象和联想来产生形象的感受。其描绘手法通常具有普遍性,如《舍赫拉查德》中带有宣叙调特点,由三支长号和一支大号奏出表现阴残凶狠的苏丹形象的音响,和带有阿拉伯音乐节奏特点、以及东方音乐特有的妩媚色彩的乐曲所描绘的蒙着面纱的少女的聪慧迷人的形象对比;巴托克的交响音画《两幅肖像》中对同一人物的两副不同嘴脸的描绘;舒曼钢琴套曲《狂欢节》中对十个不同人物形象的描绘等等,无一不可唤起欣赏者得到鲜明可感的形象感受。音乐对大自然景色的描绘主要借助于大自然音响的模拟和空间境界的暗示,启发欣赏者联系生活经历来联想。如像德彪西的交响素描《大海》,罗西尼的《威廉•退尔》序曲等乐曲中对黎明、大海、田原、山林、暴风雨、黄昏等自然景色的描绘,无一不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总之,音乐是借助描绘现实外部特征,体现人的思想感情,并以独特的方式对生活现象进行美学评价,向欣赏者暗示、象征或比拟主客观世界的一切现象。如由音乐描绘的皎洁的月光、微波粼粼的海面、黄昏的到来等大自然景象,可能在欣赏者心中产生诸如冥想的柔情、悲伤的吟诵、焦虑的心境、阴暗的预示等情感活动的感受或反之;由音乐描绘的诸如呼啸的狂风,翻腾的巨浪、奔腾的骏马等场面,也可能在欣赏者心中产生诸如情感的冲动、坚强的意志、心底的申诉、悲愤的呐喊、与命运的抗争等情感活动的感受,也或反之。繁声竞奏,欣赏可以在横的欣赏比较中提高自己的欣赏水平。同时,也不仿作纵的透视。例如,春天是古今中外作曲家的见主题。贝多芬的十首小提琴奏鸣曲中最受欢迎的《春》是古典音乐中表现春天的典范。但在欣赏时却让人几乎感受不到有什么写春景的因素,而主要表现贝氏青春时期对春天的感受,充满了蓬勃的朝气和乐观的情绪。如果说格里格的钢琴小品《春潮》让人感受到北欧春天的清新温暖气息,那么拉赫玛尼诺夫的浪漫曲《春潮》便如是滚滚春潮奔腾,给人以火样的热情。民乐曲《春江花月夜》则是通过优美如歌旋律,谈雅妩媚的韵味,细腻地刻划了人在月夜春江的迷人景致中悠然自得的情趣。李焕之的《春节序曲》又把春天作为新社会的象征,让人感受到充满欢欣鼓舞的情绪。这许多的通今古之邮,欣赏者可获得深层的美感,欣赏境界当可层楼更上。可见这类知识的积累具有现实意义。
音乐欣赏能力的提高,与欣赏者生活阅历的丰富也分不开,欣赏者直接或间接的感情与生活经验,一方面有助于欣赏指向的正确。例如《天鹅》这首著名乐曲。一经发表便广为流传,并被改编成多种艺术形式以传播,尤以根据该曲编演的芭蕾舞《天鹅之死》这样悲哀的感受。该曲是圣一桑《动物狂欢节》组曲中,唯一不带漫画和戏谑色彩的乐曲。在该组曲的若干小曲中,作者曾将当时一些音乐大师的名曲片断揉合其中,并加以夸张变形冠以动物的曲名。可以这样理解:作者当为自己在愉快的休养中创作的“恶作剧”而感到自豪——对当时的音乐生活作了善意的戏谑和尖刻的潮笑。而《天鹅》正是作者对自己“出污泥而不染”的高尚品格的写照和总结。事实上,众多作曲家笔下的天鹅,并不是动物园中一般的飞禽,往往是人性化了的形象,具有人的崇高、善良的优美品性,充满着人的真挚、深沉的丰富感情。难道不是吗?——从天鹅洁白的羽毛、悠闲身姿中,从人们熟知的天鹅的高贵品格中,“提炼”出高雅的气质,幻化成各具风格的旋律:柴可夫斯基的舞剧《天湖鹅》配乐,诚挚而恳切;挪威戏剧家易卜生作词,格里格谱曲《天鹅》清高而明静;而圣—桑这首《天鹅》则显得恬静典雅。由此只能认为,芭蕾舞剧《天鹅之死》虽然对舞剧来讲是成功的,但其所表现的中心内容,却是因编者生活及感情经验欠缺而引起的对配乐乐曲感情内涵的曲解,从根本上违背了乐曲所表达的基本的感情性质。
另一方面,有助于欣赏内涵的丰富和欣赏力的深化。如对同一音乐成品的欣赏,常常会因为欣赏者的感情经验和生活经历的丰富以及阅历的加深而对音乐得到新的领悟,获得深化的美感体验,英国音乐家柯克曾以自己的欣赏活动为例:“我自己(以及他人)对莫扎特的大调作品的理解曾经是:(1)童年时期,悦耳的音乐;(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