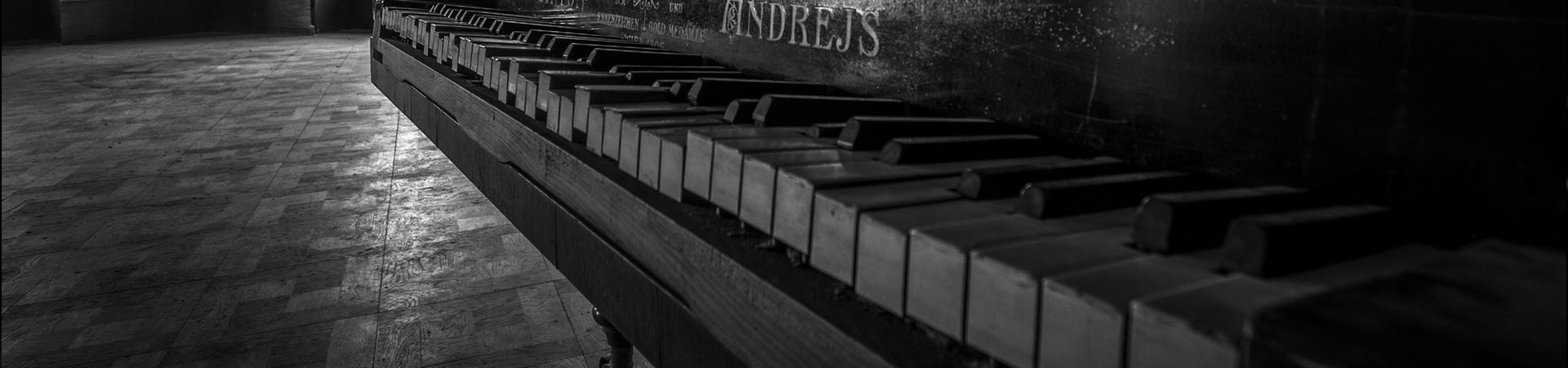艺术考级本身没有错,应该反映儿童的艺术修养也没有错,但在执行过程中部分环节上出现了很多纰漏,其中既有不科学的地方,也有不合理的地方,还有功利过多的地方。艺术考级在落实教育方针时,有功劳,有苦劳,也有失误。可是,小孩脏了要洗澡,洗完澡要把脏水泼掉,可不能把小孩也泼掉了呀。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最初从音乐学科兴起实行了考级制度,最后扩展到艺术诸多门类,林林总总,开始仅有北京五家考级机构,后来各地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截止到去年,全国大约有百余家考级机构。从历史的纵向来看,实行艺术“考级制度”可以称得上一项“丰功伟绩”—短短十几年,我国艺术教育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普及,这在历史上绝无仅有,目前我国拥有数百万计的艺术学习者,这在世界上可谓“超级大国”。
近年来,“考级”成了众多琴童和家长们口头上的高频词,同时一些说法甚嚣尘上。诸如“某地考级出现考生可任选考查内容,考级结果为百分之百通过率,达不到所报级别规定水平者可降级授予通过证书”;“某地琴行承办考级,考官们一专多能,同时为键盘、管乐等多种乐器担任主考”;“连续十几名考生演奏作品调性不分、张冠李戴,原来他们出自同一当地名师之门……”
为此,本刊记者一行近日数次深入考级现场,走访了在全国广有影响的数家在京考级机构的近十名行政官员、主考官,以及全国知名的音乐家和文化部主管部门的有关领导,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文字能够引起更多的人们静下心来思考发展中的问题,让我们的考级“热”保持持续性的健康发展。
音乐考级大家说
2004年2月北京市某音乐考级机构考级现场
“我的孩子这次参加琵琶六级考试,由于去年‘非典’耽误了,所以这次是跳级考试。虽然也知道跳级对专业学习并不好,可是没办法,孩子明年就上初一,就更没时间了,我们想在初中阶段就让她把九级‘赶’出来。” 陪同孩子考级的张先生说,“考级总体来说是件好事,我们家长不懂,孩子考出级来就觉得钱没有白花、时间没有白费。今年不知怎么回事,突然跳级要加收前一级的全部费用,再加上报名费,仅考级也要花掉一笔不小的费用,而在另外某某机构跳级考试却不加收任何费用。另外以前考级通过证书就只发一张纸,现在每次都要发证书,交上15元的证书费,其实真的没必要,现在家里的证书又放一摞了。”
带孩子参加管乐考级的王先生说:“今年不知怎么回事,把考级的时间安排在开学第一天,又是星期一,这不,我们全家都请假出来了。孩子学习音乐只是想发展业余爱好,不想耽误文化课学习,但又报了名,不得不来,所以,希望将来考级主办方能和教委提前做好沟通,尽可能避免这种时间上的冲突。我的孩子平时很少有登台表演的机会,我们不懂专业,真希望将来在孩子考级的时候能够旁听,亲耳听到专家对他们水平的评价。”
当记者问到为什么考级的话题时,一位家住北京宣武区的李先生直言不讳地说:“现在身边朋友的孩子几乎都在学琴、考级,大家碰到一块儿就谈某某的孩子过了几级几级,自己的孩子没考级或考的级别太低,就觉得孩子比别人家的笨,连自己都仿佛矮了半头似的。”
正在上初三的李伊,这次要拿下钢琴的九级,她妈妈介绍说:“她每天回家先练琴50分钟,然后吃饭20分钟,写作业至深夜。现在孩子学习很好,之所以选择考级,就是想让孩子知道不吃苦中苦,难得甜上甜,考级就是对她意志力的磨炼。”
我们随后又采访几位辅导教师
刚走出高校校园的年轻钢琴教师吴月月似有苦衷地说:“为了满足部分家长‘速成’的心理,在学生基本功不扎实的情况下,教学中我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和学生一起‘磨’考级曲目,结果是考级通过了一定级别,但越往后学习越是寸步难行,更别说视奏、演奏能力的提高了。实际情况是这样,我不这样教,他就会马上另请高明,不跟你学了。”
中国戏曲学院手风琴教师孟茜深有感触地说:“起初学琴考级是为了达到规范化为目的,但久而久之,考级教程竟变成了大多数教师的教学大纲。为了考级,教师、学生、家长围绕每年考级教程中仅有的几首作品转圈,除了考级教程中的这几首作品,其他作品几乎无人问津。这样教学双方均以考级为惟一目的,确实使学琴的孩子们越来越远离了学习音乐的乐趣。另外,音乐是抽象的艺术,它永远不可能像1+1=2一样绝对化,所以考级教材虽然经过专家们反复推敲,但它仍不能真正作为乐曲难易程度的惟一标准而被运用到教学中。事实上,有许多精致的小品完成好也是相当不容易的。与此同时,在众多学琴的学生们对音准、风箱、节奏、强弱等内容疲于奔命的同时,真正对音色的品味,风格的把握,细腻程度的琢磨,早已被人们抛之脑后,教学双方失去了音乐欣赏的时间。 ”
在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读研究生的小提琴教师武惠说:“在教学实践中,我常有这么两个问题困扰于心:一是考级标准上虽有各种明确规定,但由于音乐表演不能像笔试一样有统一的试卷与答案,考试必然带有主观性。同样或不同的考官,不同时间、地点,精神状态、身体状况都是可能变化的因素,另外还不排除一些与考官老师有“关系”的考生,他们与其他人的标准是否一致?我们对考官们不论在何种情形下对考生一视同仁的要求恐怕太苛刻。二是考级的区域差异性。由于是全国性的非笔试考试,地域差异肯定存在。当然,考级委员会的老师们一直在努力消除这种差异,但仍不能排除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地方。对于不同地区的考生来说,就不可能完全公平。”
曾在中国从事多年钢琴、小提琴教学工作的日籍钢琴教师高桥雅江在比较了中国、英国艺术考级后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中国的音乐考级较之英国皇家音乐学院的考级从机构到体制都尚未完善:各地钢琴考级有九级封顶的,也有十级封顶的,收费标准也各不相同,有些地方还出现了单位之间的恶性竞争。”“国内外考级的考官评委相差悬殊。英国皇家音乐学院的考官,都是由专业教授组成,都有着严格的职业规范、规矩和评定规则。国内的情况就大不相同,有的考级单位不顾专业,只要稍懂点五线谱的人员就可以去当考官(记者心语:有待考证?),是二胡专业,却充当钢琴考级的评委,有的甚至拿着谱子当考官。”“如英国皇家音乐学院,为了让学生轻松参加考级,在考场里的每个考官始终都面带微笑,举止文雅亲和,以致有些考官一天下来,因为长时间的微笑脸部肌肉都无法复位。相比之下,在中国我所见到的考官大多缺少亲和力……有时遇上修养差的考官,根本不讲起码的礼仪,只求快、快、快……”
通过采访,记者深刻感受到了百万琴童、家长和教师们对我国音乐考级的极大关注,更多的是困惑和期待。著名小提琴演奏家盛中国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目前很多家长把孩子的音乐考级看得太重,甚至因为一些家长的虚荣心和一些考级机构及老师的惟利是图,把孩子学音乐的天赋扭曲了。”可是,我们真的能责怪那些望子成龙、一腔热忱的琴童家长吗?又有谁能告诉他们究竟路在何方呢?
驻京